父亲去世伯父娶了母亲现仨人都走了,我和小弟因他们的合葬难住了
父亲去世伯父娶了母亲现仨人都走了,我和小弟因他们的合葬难住了
三人行——记忆的合葬
"小聪,这块墓地到底合不合葬伯父?"弟弟问我,声音哽咽。
我站在父母合葬墓前,一时语塞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块已经不走时的上海牌手表。
墓碑上父母的照片泛着黄,经历了太多风吹日晒。那是七十年代初拍的,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母亲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确良衬衫,头发齐齐地盘在脑后,脸上带着羞涩的微笑。
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深秋,天气转凉得格外快,老槐树的叶子簌簌往下掉,像是在为即将离去的生命哀叹。
父亲周长山因肺病走得突然,前一天还在院子里劈柴,说今年冬天要来得早,得多备些柴火。隔天就倒在了厂里的车间,医生说是尘肺加重,抢救无效。
留下母亲李巧云带着我和弟弟周小明艰难度日。那时候我十二岁,小明才八岁,对这个世界懵懂无知,只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,家里的煤油灯似乎也比从前暗了许多。
母亲在纱厂做工,一个月工资不到四十块,领回的粮票勉强够我们吃饱。那时候,能在锅里看见油星子就是好日子了。
记得父亲下葬那天,铁岭的天阴沉沉的,就像被泼了墨。乡亲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裳,低声议论着"这么年轻就走了"、"可怜巧云和两个娃娃"。
伯父周长河穿着同样是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手里攥着一方已经湿透的手帕,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。他站在坟前,一言不发,只是肩膀不停地抖动。
"大哥,你走得太早了。"最后他只说了这一句,声音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。
父亲走后的日子,一天比一天难熬。冬天的夜格外长,我们家的煤炉子总是不大旺,为了省煤,母亲常常等我和小明睡着了才生炉子,自己缩在一旁缝补衣服。

有天晚上我醒来,看见母亲在豆大的煤油灯下用针线缝着什么,眼睛里闪着泪光。那一刻,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心酸,像是有人在我胸口狠狠地揉了一把。
就在这时,伯父开始常来我家,帮着劈柴、挑水、修缮房顶。他是拖拉机站的机修工,手巧心细,单身一人,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。
"巧云,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辛苦,我来帮你。"伯父总是这样说,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温柔。
起初,我以为这只是对兄弟家庭的照顾,后来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有时候我放学回家,会看到伯父和母亲肩并肩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,说着些低低的话。
伯父会带来一些稀罕物件,比如城里才有的糖果、小明最爱吃的开口笑,还有那时候难得一见的香蕉。有一次他甚至带来一个收音机,那可是整条街上都少见的玩意儿。
"给孩子们听广播,长点见识。"伯父摆弄着收音机的旋钮,调到了地方台在播的评书节目。那天晚上,院子里挤满了邻居家的孩子,大家围着那个"会说话的盒子",听《岳飞传》,兴奋得不得了。
小院里的七嘴八舌不断传来:"看那周长河,趁兄弟走了,想占便宜呢。"
"那李巧云也真是,丈夫刚走,就跟大伯哥勾搭上了。"
"可不是嘛,守寡才几个月,就有了新人,这算什么事啊。"
这些话像一把把小刀,扎在我幼小的心上。我懵懂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刺,对伯父的每一次来访都充满戒备。
上学路上,有小孩子对我指指点点:"看,那就是没爹的小聪,他妈要改嫁给他伯了。"我咬着牙,握紧拳头,忍住眼泪,在放学后狠狠地揍了那个多嘴的男孩。

"你胡说!我妈才不会!"虽然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。
回到家,母亲看见我红肿的眼圈和擦破的指关节,叹了口气,用凉水给我敷手。"长聪,谁欺负你了?"
我咬着嘴唇,不肯说。怎么能说呢?那些话比拳头更伤人。
那天晚上,母亲在厨房忙活,伯父来了,手里提着一条刚从集市上买的鲜鱼,说是给我们改善生活。
"长聪,过来帮伯父拿工具。"他唤我,语气和父亲如出一辙。
我冷着脸,故意慢悠悠地走过去,接过扳手时特意避开他的手指,就像躲避什么脏东西。
"你妈辛苦,你得多帮衬着点。"他拍拍我的肩膀,我却像触电般跳开。
"用不着你管!"我嘴上逞强,却在心里暗暗落泪。我想念父亲,想念那个会在夏天给我们扇蒲扇的、会背着我去看露天电影的父亲。
"周长聪!不许这么跟伯父说话!"母亲从厨房出来,脸色难看。
"他才不是我伯父!他就是想——"我哽咽着,说不下去了。
"想什么?说啊!"母亲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。
"街坊都在说,他想当我爸!"我终于爆发了,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母亲愣住了,伯父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
"长聪,你去看看作业本落在隔壁李奶奶家没有。"母亲低声说。
"我没去过李奶奶家!"我叫道。
"去,就说我让你去找。"母亲的语气不容争辩。
我摔门而出,但没有去李奶奶家,而是躲在院墙外的老槐树下,听他们说话。
"巧云,孩子不接受,这事就算了吧。"伯父的声音低沉。

"不行,长山临走前特意交代过,让我找个好人家,别让孩子跟着受苦。"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"可是..."
"你是个好人,长河。我看得出来。可能是我太心急了,孩子还小,不懂事。"
"不急,等他们长大些再说吧。"
我蹲在墙根,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情绪。原来父亲知道自己会走,还做了安排。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另一个人站在父亲的位置上。
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小明差点出意外那天。七九年的冬天格外冷,北风刮得人睁不开眼。厂里放了几天假,伯父带我们去拖拉机站玩,说是让我们开开眼界。
那时的拖拉机站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,院子里整整齐齐停着十几台东方红拖拉机,大人们穿着蓝色工装在忙碌,空气中弥漫着柴油的气味。
小明不知怎么爬到了闲置的拖拉机上,在驾驶座上摆弄方向盘,一脸兴奋。突然,不知是哪个零件松动了,整台机器开始晃动,眼看就要翻倒。
"小明!"我吓得叫出声。
伯父一个箭步冲上去,把小明推开,自己却被砸断了左臂。血一下子染红了他的衣袖,但他却紧紧地抱着小明,倒在地上。
大人们迅速把伯父送往医院,一路上小明哭得不成样子,我也吓得脸色发白。医院里,伯父疼得满头大汗,却还笑着说:"没事,男人嘛,断胳膊总比断了心肠好。"
那一刻,我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为了救邻居家的孩子,从梯子上摔下来,扭伤了腰。那时他也是这样,疼得龇牙咧嘴却还安慰大家别担心。
伯父住院的那段日子,母亲每天都去医院照顾他。我和小明放学后也去,看见母亲端着洗脸水,小心翼翼地帮伯父擦脸。

"长河,你这样我怎么跟长山交代啊。"母亲红着眼圈说。
"傻话,我是他兄弟,照顾你们是应该的。"伯父看向我和小明,眼神温柔。
我第一次没有躲开他的目光。
出院后,伯父右手拿着一个旧皮箱来到我家。箱子有些陈旧,上面的锁扣已经锈迹斑斑,但能看出保管得很仔细。
"长聪,这是你爸的东西,我一直替他保管着。"他艰难地用右手打开箱子。
箱子里有父亲年轻时的照片,黑白的,边缘已经有些泛黄。照片上的父亲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,意气风发,和我记忆中那个总是疲惫的身影判若两人。
有他写给母亲的信,纸张已经变得脆弱,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见:"巧云,我在部队一切安好,勿念。听说你在大队干得不错,我很高兴。等我转业回来,我们就成家,好吗?"
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——那是父亲最值钱的东西,他生前从不离身。
最下面是一张发黄的纸,上面是父亲的字迹:"长河兄,若我有不测,请照顾巧云和孩子们。你是我最信任的人,知道你会做得比我好。"
落款是1978年,父亲去世前几个月。
那一刻,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原来父亲早就知道自己时日不多,他把最心爱的人托付给最信任的兄弟。而我却一直用恶意揣测着这份情谊。
"你爸这块表,是他当兵时立功得的奖品,他一直很爱惜。"伯父轻轻拿起手表,递给我,"现在,这是你的了。"
我接过表,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,那不仅是金属的重量,更是一种责任和传承。
那晚,母亲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终于开口:"长聪,伯父对我们很好,他是个正直的人。你爸生前也说过,如果他不在了,希望我能找个好人家,别让你们跟着受苦。"

"那为什么不早说?"我质问,声音里带着委屈。
"我怕你们接受不了,怕辜负你爸。"母亲眼里含着泪光,"可后来我发现,你爸和你伯父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同样的善良踏实。我想,你爸在天上看到了,也会安心的。"
母亲拿出一个绣着喜鹊的小荷包,从里面取出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是年轻的父亲和伯父,两人穿着一样的工装,站在厂区门口,笑得灿烂。
"这是你爸和伯父刚参加工作时照的。那时候他们都是厂里的模范,你爸后来因为肺不好才转了岗。"母亲抚摸着照片,"他们兄弟感情特别好,从小相依为命,没想到..."
她的声音哽咽了。
那年过完春节,母亲和伯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没有大操大办,只是请了几家邻居吃了顿饭,蒸了几屉白面馒头,炖了两锅肉,已经算是很讲究了。
村里人的闲话渐渐少了,因为大家都看在眼里——伯父待我们如亲生,每月工资几乎全部上交给母亲,自己的烟也从大前门换成了便宜的红塔山。
小明很快亲切地叫他"爸",伯父每次听到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只有我,仍倔强地称他"伯父",却在心里慢慢接纳了这个家。
八十年代中期,家里添置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,是伯父从厂里福利处好不容易申请到的。那天晚上,全院子的人都挤到我家来看《西游记》,大人小孩笑得前仰后合。
伯父坐在角落里,安静地看着大家,脸上是掩不住的欣慰。我悄悄走到他身边,第一次主动叫他:"爸。"

他愣了一下,然后眼圈红了,粗糙的大手轻轻揽住我的肩膀。那一刻,什么话都没说,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们家的生活渐渐好起来。小院里种上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月季,每到春天开得热闹。伯父用废弃的自行车零件给我做了一个书架,终于不用把书堆在炕上了。
"好好读书,考上大学,比你爸强,比我强。"伯父总是这样鼓励我。
八八年,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临行前,伯父塞给我一个布包,里面是一沓整整齐齐的钱。
"这是我这些年省下的,你拿着,在外面别委屈自己。"他说话时眼神闪烁,像是害怕我拒绝。
我知道这钱来之不易,是他一包接一包烟省下来的,是他放弃了多少顿肉菜省下来的。
"谢谢爸。"我轻声说,这一次,这个称呼终于叫得自然而然。
岁月如流,一晃三十多年过去。我和小明都成家立业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母亲先走的,肺炎,走得很安详;伯父没过几年也去了,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是想念母亲;父亲病逝已近四十年。
如今他们三人都已作古,只留下我和小明站在墓前,为一个合葬的决定而发愁。伯父的骨灰盒静静地放在我们脚边的木箱里,等待着最后的安置。
"怎么样,大哥?"小明问我,声音有些哽咽。
我低头看着父母的墓碑,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的话:"你爸和你伯父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。"是啊,他们都是那个年代里普通而又伟大的人,肩负着责任,默默付出,不求回报。
"合葬吧,小明。"我终于开口,"他们三个人,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,相互扶持,共同撑起了我们的家。现在,也该让他们在地下团聚了。"

小明点点头,眼里闪着泪光:"伯父——不,是爸,他对咱们真的很好。记得我上初中那年,他硬是跟厂里请了半个月假,天天接送我,就因为路上有几个小混混总欺负我。"
"是啊,他二话不说就认下咱们这个家。"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上海牌手表,表盘已经有些模糊,但雕刻在背面的"永不言弃"四个字依然清晰。
"咱爸和伯父,都是这样的人。"我抚摸着表面,仿佛能触摸到那段逝去的时光。
我们请来村里的老师傅,重新修整了墓地,在原有的墓碑旁加上了伯父的名字和照片。照片是他六十岁时照的,穿着整齐的中山装,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,眼神依然和蔼。
师傅把三个骨灰盒一起放入墓穴,上面覆盖上新土。我们按照老家的习俗,摆上三杯酒,三双筷子,三碗饭。
"爸,妈,伯父,你们在下面要好好的。"我俯下身,轻声说道。
"大哥,你记不记得那年春节,咱家第一次包饺子?"小明突然问道。
我笑了:"记得,伯父包的饺子丑得像元宝,但他说那样吃了能发财。"
"还有那年,他瞒着咱妈,偷偷带我们去游乐场,结果回来晚了,被咱妈骂了一顿。"
"是啊,他从来不跟咱妈顶嘴,只是笑呵呵地说'孩子高兴就好'。"
我们站在墓前,回忆着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子。风轻轻吹过,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,仿佛是他们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。
"大哥,你说他们三个人,谁最辛苦?"小明问道。
我想了想:"都不容易。爸年纪轻轻就走了,来不及看到我们长大;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,还要面对外人的闲言碎语;伯父接手了别人的家,付出了那么多,却从不求回报。"

"是啊,那个年代的人,都不容易。"小明叹了口气。
我掏出当年伯父给我的上海牌手表,轻轻放在墓碑前:"这表,陪了三个人一辈子,现在也该回到他们身边了。"
这块表见证了我们家的悲欢离合,见证了那段艰难岁月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。
"大哥,你说咱们现在生活好了,他们知道吗?"小明问道,声音里透着一丝遗憾。
"知道,他们一定知道。"我看着墓碑上三张熟悉的面孔,仿佛看到他们在月光下围坐在一起——父亲的坚毅,母亲的温柔,还有伯父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。
在这个世间,他们用平凡的生命,诠释了最不平凡的情感。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,但却如同山间的小溪,润物无声,滋养着我们的心灵。
"回去吧,孩子们还等着呢。"我拍拍小明的肩膀。
夕阳西下,我们沿着乡间的小路慢慢走远。身后,三座合为一体的坟茔安静地矗立在山坡上,见证着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,也见证着那个艰难岁月里人性的温暖与坚韧。
春风拂过墓碑,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那是生命的气息,也是人间最朴素的情感,穿越时光,永不褪色。
-

- 炒菜炒出毒药?毒铁锅为何屡禁不止?如何鉴别这要命的铁锅
-
2026-01-30 13:51:08
-

- 农村老汉称朱德为老朱,两人是何关系?为何差距如此之大?
-
2026-01-30 13:48:53
-

- 来自世界各地的引人注目的边界图像,真叫天壤之别
-
2026-01-30 13:46:39
-

- 袁殊:中国隐蔽战线的间谍之王
-
2026-01-30 13:44:25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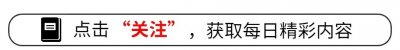
- 中国吉林省著名旅游景点攻略
-
2026-01-30 13:42:10
-

- 武德充沛?还是毁誉参半?详解米格-23可变后掠翼战斗机
-
2026-01-30 13:39:56
-

- 世界常规动力航母的巅峰——已经退役的美国“小鹰”级航空母舰
-
2026-01-30 13:37:42
-

- INFINITE STRATOS轻便小说系列将在第13卷结束
-
2026-01-30 12:28:00
-

- 荥阳市贾峪镇:“三力”齐发,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安置社区建设
-
2026-01-30 12:25:46
-

- 温暖男朋友的简短情话 对男朋友说的暖心的小情话简短
-
2026-01-30 12:23:32
-

- 松下ups蓄电池寿命(松下ups蓄电池回收价格)
-
2026-01-30 12:21:17
-

- 人过四十,莫管二事, 人过五十,莫管二人
-
2026-01-30 12:19:03
-

- 北京“改名”最成功的高校,以前名声不好,现在受到外地学生欢迎
-
2026-01-30 12:16:49
-
- 为什么会出轨脑科学解释(出轨的根源是双方彼此感觉好)
-
2026-01-30 12:14:34
-

- 身份证年龄比档案年龄小能退休吗(档案年龄小身份证大能办理退休吗)
-
2026-01-30 12:12:20
-

- 榴莲冷冻好吃还是冷藏好吃(介绍榴莲保存技巧)
-
2026-01-30 12:10:06
-

- 赫赫有名的十大命格最厉害的命格
-
2026-01-30 12:07:51
-

- 去追一个女生让女生感动的话(追女生让女生感动的话)
-
2026-01-30 06:02:09
-

- 主动了你就有机会 和金牛座女生聊天话题
-
2026-01-30 05:59:55
-

- 气场全开的易大佬
-
2026-01-30 05:57:40



 otc是什么意思(OTC是什么意思?深入解析OTC市场)
otc是什么意思(OTC是什么意思?深入解析OTC市场) galgame鉴赏:十二魔器之一 重口猎奇作《解体插入新书》
galgame鉴赏:十二魔器之一 重口猎奇作《解体插入新书》 ky是什么梗?ky到底是什么意思?
ky是什么梗?ky到底是什么意思? 28位短剧型男,其中最高的192cm,真的是又高又帅又会演!
28位短剧型男,其中最高的192cm,真的是又高又帅又会演! “最美丈母娘”赵柯的坎坷成名史,和她的心酸情史
“最美丈母娘”赵柯的坎坷成名史,和她的心酸情史 唐朝刺史是几品?唐朝刺史相当于现在什么官
唐朝刺史是几品?唐朝刺史相当于现在什么官 略备薄酒还是略备薄宴 略备薄酒以小酌的意思
略备薄酒还是略备薄宴 略备薄酒以小酌的意思 难得的好小品演员,黄杨 在饭米粒儿中饰演黄小黄
难得的好小品演员,黄杨 在饭米粒儿中饰演黄小黄 《青涩的体验》:深刻描述了青春期的微妙情感
《青涩的体验》:深刻描述了青春期的微妙情感 玉化砗磲手串一般多少钱?这份价格清单请收好
玉化砗磲手串一般多少钱?这份价格清单请收好